热门故事
两只山雀啁啾没唤起我雅赏,倒是林地上那烂漫的金菊情锁我的双睛。蓦然想起宋人张孝祥的那句“冉冉寒生碧树,盈盈露湿黄花”,不禁肃然。古人总是赞赏菊的玉节光华,抚慰初始的清纯。时光抛人,命途多舛,追思那流逝的不在,谁说只是词砌不是心音呢!
见过太多富足或贫穷、敏锐或迟钝、深具魅力或眼界贫瘠的存活者,却很少能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简单快乐的人。我们习惯被世俗贴上诸多标签,在日复一日的现实齿轮中逐渐背负起成年人的利弊抉择,默认平庸,或过分鸡血,并从中试图获得成就感,但往往正是容易在这追逐扣篮的紧张情绪下,丢失本来的自我。
我扭转头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听见他被人叫白痴时我是怎样的伤心,即使是开玩笑——噢,至少是半开玩笑;可是我自己往往认为他就是个白痴。尽管我自己的牌很糟糕,我却深谙牌道,完全可以断定他的牌——趁他不留神时——充分说明他老婆如此冲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她发火搞得我心烦意乱,我可不能说,也不可能说为什么在她的“最新搭档”小博尔顿·伯恩对她的话报以一声尖笑时,我真想给这小无赖一记耳光;也不可能说为什么海利,德莱恩(他总是一下子听不明白人家在取笑他,然而肯定慢慢会明白)最后发出他那表示欣赏的低沉丰厚的笑声——那么为什么我偏偏要从记忆中完全抹掉这一幕呢。为什么呢?
老人提起他儿子时,脸上并没有责怪的神色,虽然有一声深深的叹气,可我总觉得这是对他自己的责备,这叹息声附带了太多,无论如何也我无法完全明白的!我想,每个父亲在对自己孩子失望时都会有一声这样的叹息!不知道父亲看到我那年高考成绩时的叹息,是不是也是这样沉重!
钟义和母亲住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山村里。钟义天天上山打柴。住在这一带的人本来生活得不错。这几年来了个九头鸟的妖怪,可把人们害苦了。



_20240310021608A38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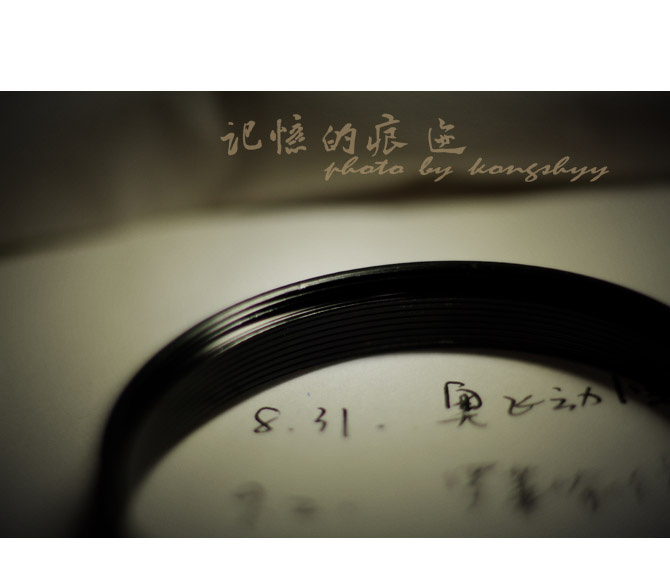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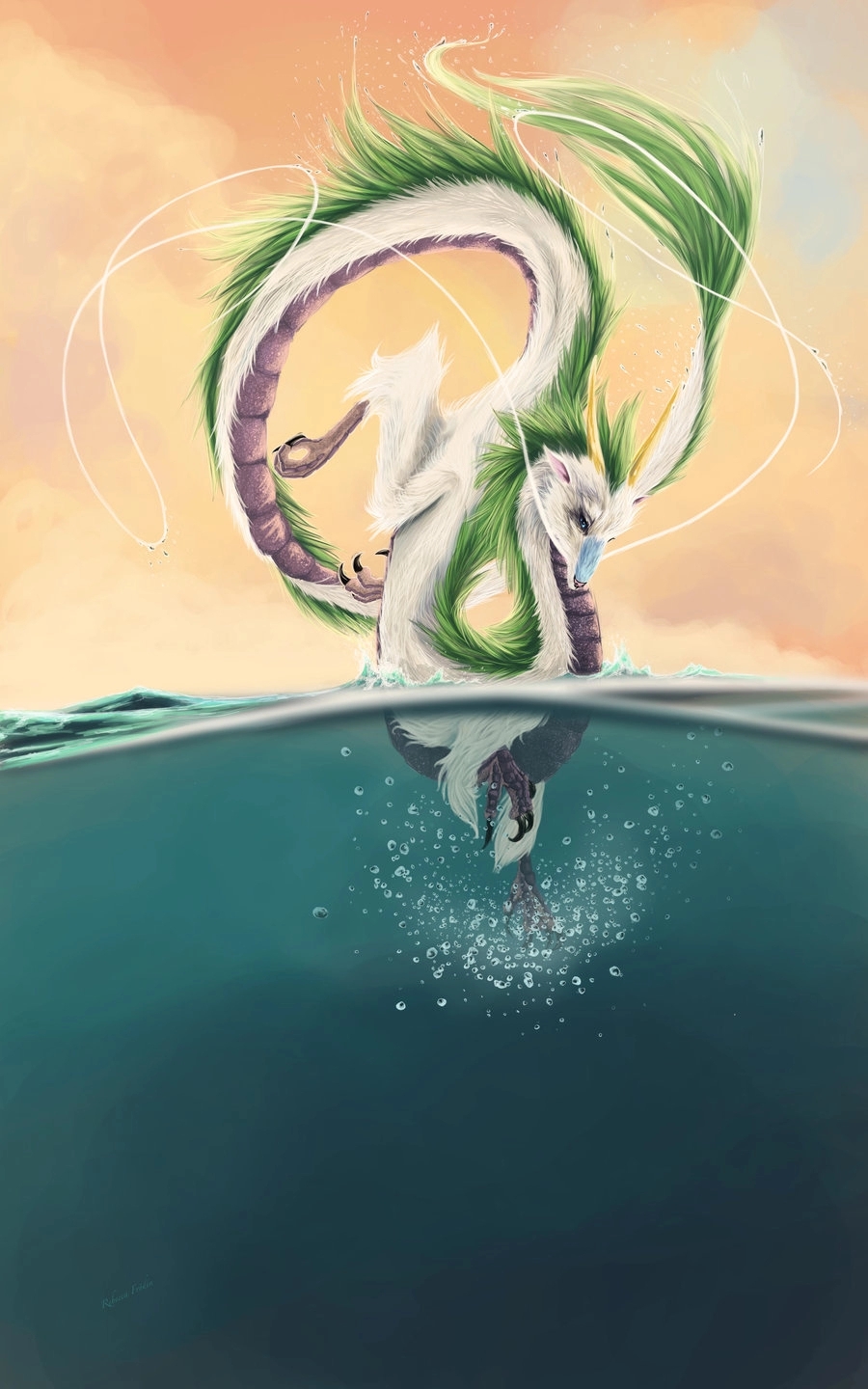
_20241115233648A163.jpg)
 6.7
6.7_20241115231901A12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