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固集的乡绅们
郭固集作为华北平原腹地一个普通村落,规模远比周边的自然村落大得多,但在官方眼中,它仍不过是一处自然村落。因此,王朝时代的官方对它是没有丝毫兴趣的,既没有为其派遣过类似今天的村长支书一类的公共管理者,好像也从未有过上级领导到此公开视察或微服私访。郭固集人一直在自己管理自己。因此,郭固集的历史像郭固坡无处不在的蒿草疙疤秧的历史一样,是一场场自生自灭的自然史。
不过,也有研究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学者说,恰是这样表面散养式的政府管理方式,让中国王朝时代的农民们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并诞生了最古老生命力也最顽强的村民自治形式——乡绅治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所谓村民自治管理制度,不是什么新发明,不过是王朝时代乡村公共管理制度的狗尾续貂。遗憾的是,注重文人政治的乡绅治理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到了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到了一个道德不再具备优势的时代,畸变成了强势者甚至恶人霸王控制乡村的丑剧。
也有学者说,乡绅治理模式,将天理、国法、人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崇尚文明道义的力量,尊重正统文化和文化人,于是,王朝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既有制度的冰冷严苛,也有人性的温情脉脉,其对民事刑事争讼的判决,往往让人心服口服。“乡绅”一词和它所代表的人群,在王朝时代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和文明群体,是深受民众敬重的词汇和群体。然而,经过形形色色革命的洗礼,乡绅一度成了土豪劣绅的代名词,今天人们印象中的乡绅,多为戴顶瓜皮帽、戳根儿文明棍、外表道貌岸然、骨子里男盗女娼的虚伪奸诈之辈。当然了,如此鼠类而混进乡绅队伍的,并不少见,但总体来说,乡绅主体是本地退休官僚、本乡本土知名人士,而王朝时代的官僚,多为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科举出身;土著名士,也多为博学识礼的优秀人材。这就决定了中国王朝时代村民自治制度的质量,非礼崩乐坏社会基础上同名制度可比。
因为缺少文字可考的历史,郭固集在王朝时代出现过哪些学而优则仕的乡绅名人,已无从查考。
有村民说,他爷爷的爷爷说过,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一位读书人,满腹经纶,满腔仁义礼智信,还曾经进京科考过。他并且自豪地说,他家中早些年还珍藏着一块举人牌,只是在文革中被他奶奶主动填进锅底当了柴火。他还向乡亲们出示了可以证明他的书香门第的祖传宝贝——一摞老厚的绵纸线装书。遗憾的是,那只不过是一套康熙字典和几本旧学发蒙读物,比如《幼学琼林》、《千字文》之类,仅仅靠这些玩意儿,估计是中不了科举入不了仕的。
笔者故去多年的姥爷曾经是郭固集地区不多的读书人之一,并且因为识文断字,被一位在外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的红色革命上线乡亲发展为革命下线,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胜利后,做了级别很低的政府机构公务员,虽然不是通过科举学而优则仕,终归还算沾了读书的光。然而,他老人家也不过是年少时在郭固集西邻孟庄村的孟夫子私塾中读过几年四书五经罢了,放到科举时代,估计只能混上个没有学位不包分配的穷秀才。
郭固集学而优则仕的乡亲,只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才开始有名有姓的。我姥爷说过,他记事中,郭固集五道街最了不起的学问家并学而优则仕的乡亲,是西街刘家的刘润三先生。刘家家境殷实,从而得以将族中优秀子弟送到外边上大学读大书。刘润三乡亲先是在济南府读书,后来又去了京师大学堂,并在北京走上红色革命道路,并且在革命队伍中混得风生水起,好像曾经在中共平原省委担任过要职。可惜的是,这位郭固集杰出乡亲在济南乘火车,被火车撞伤腿脚,落下病根,后来竟然因此恶化并要了刘杰亲的命。天妒英才啊!
到了刘润三下一辈,刘家又出了一位在郭固集响当当的乡亲——刘耕读。当刘家长辈刘润三先生在锤头镰刀的红色旗帜下叉腰高声讲话的时候,他的同族后生刘耕读正在青天白日旗帜下津津有味地听着老蒋小蒋俩先生的训导。刘家祖坟风水旺盛啊,子孙竟然红白通吃。因为活在中国当代史中,白色的刘耕读乡亲的知名度远比他的红色长辈高得多,直到今天,郭固集乡亲还在盛传他的传奇故事:刘耕读和小蒋是同学,蒋往台湾跑的时候,非要拉着刘乡亲一块儿走;无奈,刘眷恋故土不走,二人遂在一座桥下像一对儿恋人一样洒泪惜别。
传奇真假不知道,货真价实的是,从1957年反右,刘耕读乡亲就开始了他此后漫长的被流放生涯:从三十多岁的中年开始,戴着右派的高帽子,从南京灰溜溜地下放到了郭固集老家。先是料理生产队的菜园,接着在离村八里远的专业队看庄稼。好在,乡里乡亲的,尽管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但乡亲终归是乡亲,不管刘乡亲戴着什么颜色什么型号的帽子,乡里乡亲对他总算不薄。只是,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跟着他妈并姓了姥姥家的姓,母子呆在南京,从未在郭固集留下哪怕一个脚印。更凄怆的是,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落魄文人,基本生活几乎难以自理,孤独得肯定前心挠后背的中年刘乡亲常常不能把窝窝头蒸熟,常常在感冒的时候,只能像西方人一样靠着狂喝凉井水治疗……
就这样,一晃二十年!
二十年的郭固集菜园风光和郭固坡大野风光,在中年的刘乡亲面颊上刻下了一道道浅浅的、深深的皱纹,把一名想必原本意气风发、喜欢高声演讲的青年演讲家教训成了言语木讷、目光呆痴的庄稼老汉……
好在,“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在1970年代末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刘乡亲因此也获得了另一阶段的新生命,并被补发了拖欠二十年的工资。看到刘乡亲领回的大把钞票,有乡亲和这老头儿开玩笑:这么多年的工资一齐领,等于国家给你存起来了,好事啊!听到此话,刘乡亲顿时老泪纵横!
史无前例的“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目的就是要从肉体到灵魂地教育阶级异己分子。刘耕读这位学而优则仕的白色郭固集乡亲,用二十年的岁月喇叭是铜锅是铁地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不但从肉体,而且深入骨髓,深入灵魂。
相比较而言,当“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发展到了又一个新时期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开始变换了形式,对于革命队伍中人,尤其对于那些学而优则仕地进入革命队伍中的原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再灵肉双重教育,而更多地注重灵魂的挽救。
郭固集南北街的杜乡亲,也算是学而优则仕的有出息的乡亲。通过读书上大学,杜乡亲三十刚出头就做了临近一个乡的乡长。喜欢依靠人民群众的执政者在20世纪末期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殡葬改革运动。什么是殡葬改革呢?就是由华北平原传统的入土为安的土葬,改为入炉化灰的火葬;谁家的老爹老娘爷爷奶奶死了,必须拉到县城新建的火葬场烧成灰;偷偷地埋了,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继续烧!非烧成灰不算拉到,非烧成灰不算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老奶!好厉害,好害怕啊!
且不说殡葬改革的进步性和必要性,也不说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心理承受程度的关系,更不说其中的猫猫腻腻,只说说杜乡长的任务和由这任务带来的郁闷。
上级规定了全乡的火化尸体条数,完不成,乡长就别想当了;不当还不算拉到,想溜都不中,完不成,党纪国法不是吃素的!“就是把你们自己烧成灰,也要完成火化尸体任务!”上级有关领导在全县殡葬改革动员大会上对各乡镇负责人如此训话。
为完成任务,学而优则仕、文秘出身、斯文儒雅的郭固集子弟杜乡亲杜乡长牙一咬心一横:“挖!挖地三尺也要把死人挖出来!”杜乡长把全乡偷偷土埋的死爹死娘死爷死奶挖出来,然后,在乡政府大院里挖个坑,二十多条被挖出来的尸体堆在一个坑里,浇上汽油,烧!烧死他们!哦,不,把他们一个个给我烧成灰儿,烧成面儿!烧成黑灰儿,烧成黑面儿!然后,儿子孙子交了火葬费,把爹娘爷奶的灰儿面儿分装进一个个小黑匣子,抱走吧。抱回家后,想咋埋就咋埋,想埋多高的坟头就埋多高的坟头。
第二天早上,杜乡长正要上班,老娘突然抱住他的双腿,哭着喊着死活不让儿子走:“儿啊!我儿!这官,咱不当了;这工作,咱不要了。伤天害理啊!人家要跟你拼命啊!你娘我活了七十年了,没见过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啊!祖辈活了两千年了,没听说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
看着趴在地上紧抱儿子双腿连哭带喊的老娘,杜乡长咬咬牙,抹把泪,抽开双腿,以赴死的决绝,大义凛然地走出家门。
是什么样的一种魔力,刺激着孔孟门徒、斯文儒雅、学而优则仕的郭固集子弟杜乡亲杜乡长敢于把刚刚死去的爷爷奶奶老爹老娘生生地挖出来,浇上汽油死啦死啦地,灰儿面儿地?
是什么样的一种魔力,让孔孟门徒、斯文儒雅、学而优则仕的郭固集子弟杜乡亲杜乡长如此大义凛然,每天以赴死的决绝之情走向工作岗位呢?
如果说,杜乡长的官秩太低,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那么,郭固集学而优则仕的乡亲刘副县长和车秘书长的被教育结果,是不是有点说服力呢?
南北街乡亲刘副县长和车家乡亲省政府车秘书长与杜乡长一样,也是孔孟门徒、斯文儒雅、学而优则仕的郭固集杰出乡亲。所不同者,因为官秩较高和很高,他们是不会赤膊上阵去干杜乡长干过的那种挖人祖坟烧人爹娘的蠢事的。在较高和高高的官场上,他们涵养出了种种水平很高的道行。光荣地退居二线后,两人先后告老还乡。村中乡亲喜欢找这两位在外见过世面的杰亲闲聊,向他们咨询国家大政方针,想听听他们对国家大事国际大大事的看法。
不过,同为喝着郭固集地下水长大的郭固集乡亲,同为郭固集小学、郭固寺中学走出来的孔孟门徒、学而优则仕的杰出乡亲,刘副县长和车秘书长的闲聊方式却大大不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五十多岁就退居二线的刘副县长每逢与乡亲闲聊,总要高声牢骚,骂骂咧咧,从早起跑步的人群中开骂,直骂到晚上跳舞的人群中间;从乡里骂到县里,从县里骂到省里;含沙射影地骂,指名道姓地骂;先骂娘,后骂爹;先骂男领导,后骂女领导;男领导男盗女娼,女领导女娼男盗……刘副县长骂啊骂啊,骂啊骂啊,直骂得天清气朗,日月昭彰;直骂得年轻人跟着一起骂,小孩子跟着一起骂;到了最后,老大娘老大爷也跟着一起骂……
像刘副县长这样的退休官僚,放到王朝时代,告老还乡后是理所当然的乡村绅士,是应该主动参与到或被邀请到乡村自治管理工作中的。在竞争异常白热化的村两委竞选中,乡亲们纷纷把选票投给了刘副县长。在有些人听来也许很不顺耳的骂声,在乡亲们耳朵中,却是那样的舒坦,乡亲们巴不得刘副县长这样公道而又有威望的人在今天热火朝天而又利益纷争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中能够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黑脸主公道。刘副县长自己也有点意思想介入村民自治管理工作,像他这样曾经叱咤一方风云的高层管理者,一旦因为让位而提前退居二线,体内远未燃尽的事业激情,如果不能成为另一场事业的动力,就只能刺激着他骂骂咧咧。刘副县长这样职位较高的官员,是有道行的,他可不愿意在骂骂咧咧中度过余生。因此,对于乡亲们的选择,他很高兴地给予了尊重。不过,刘乡亲刘副县长表示,按照组织纪律,他是不能担任村两委领导的,他是党员,应该无条件地遵守组织纪律。他倒是乐意担任顾问啊、参议啊之类只管闲事不要职务更不要报酬的角色,以便为郭固集的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中晚年余热。
乡亲们皆大欢喜,当选的村两委领导却不乐意,镇领导也不乐意。村两委领导对镇领导表示,老刘搀和进来的话,俺们的工作就没法干了。镇领导找到刘副县长,拐弯抹角、可怜巴巴地央求:老领导,您就颐养天年吧,别管村里的闲事扯淡事了。如今的基层工作难搞啊,让年轻的村干部们放手去弄吧!要不然,工作推行不下去,我们镇里这些跑腿的没法向您这样的上级交差啊!
刘副县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意。他有点愤愤不平,却也只能按捺着自己老骥伏枥的春心,继续养花种草,继续骂骂咧咧,甚至更起劲地骂骂咧咧,从早上跑步的人群中开骂,一直骂到晚上跳舞的人群中。
这位孔孟门徒、学而优则仕的郭固集子弟啊,在官场干了上半辈子,告老还乡了,看来是要在臭骂中了却下半辈子喽!
省政府车秘书长就不一样了。白发苍苍的乡亲们说,车秘书长这位孔孟门徒、学而优则仕的郭固集杰出乡亲,打小喜欢谈天说地,也许有点书生意气,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吧。老了退休了,他老人家像大多数老年人一样,变得斯文安静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不过,乡亲们总是觉得,车秘书长安静得有点冷气森森,沉默得让人毛骨悚然。车秘书长不但不叫骂,一天连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愿说,除了偶尔发出一两个轻微的双音节咳嗽声“咳咳”和单音节轻叹声“唉”,想要听到车秘书长一句超过两个音节的完整话,你就等着吧,从早上跑步的人群中,直等到晚上跳舞的人群中,虽然到处可见车秘书长的身影,但你就是听不到从他喉管里发出哪怕一句两个半音节的声响。
有村民的田地被开发区征收了,一亩地只给两万块钱,村民觉得吃亏,也觉得活不下去了,但求天无路,告地无门,就哭着喊着找到了车秘书长。
车乡亲车秘书长绷着脸听了半天,偶尔鼻腔中发出类似单音节的“哼”音的恨声,偶尔眼中冒出他老人家尚有热度的火光,偶尔两眼深情地注视着倾诉的乡亲,有的还是他的近门本家。乡亲们听着看着,觉得救星就在眼前。几把鼻涕几把泪之后,乡亲们擦干泪眼擦干鼻涕,眼巴巴地盯视着救星。车乡亲车秘书长睁开沉思的双眼,看了看可怜兮兮的乡亲,半天没说话。
乡亲们忍不住催问,“叔啊,爷啊,咋办嘞?”与平常不同的是,这次,车乡亲车秘书长先是发出一个双音节的“嘿嘿”苦笑,然后,喉管中再次发出一个轻微的双音节咳嗽声,“咳咳”;乡亲们再问,又隔了半天,车乡亲车秘书长的喉管里又发出一个单音节轻叹声,“唉!”
唉!
对于车乡亲车秘书长这样的高层次退休官员,镇领导和村两委领导哭着喊着拉他当顾问当参议。他们流着真诚的热泪央求:老领导啊,叔啊,爷啊,您就行行好,顾问吧,参议吧。有您这样的金刚不坏之身压住阵脚,郭固集新农村建设遇到不管多么难啃的臭硬骨头,我们也能把它们啃下来,嚼碎了,咽下去。老领导啊,叔啊,爷啊,您就行行好,顾问吧,参议吧!
对此,车乡亲车秘书长的回答,依旧是双音节的“咳咳”、单音节的“唉”;央求得急了,车乡亲车秘书长干脆锁了老家的院门,带着车老夫人,逃回了郑州。从此,郭固集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老人家的半个身影。
唉!
咳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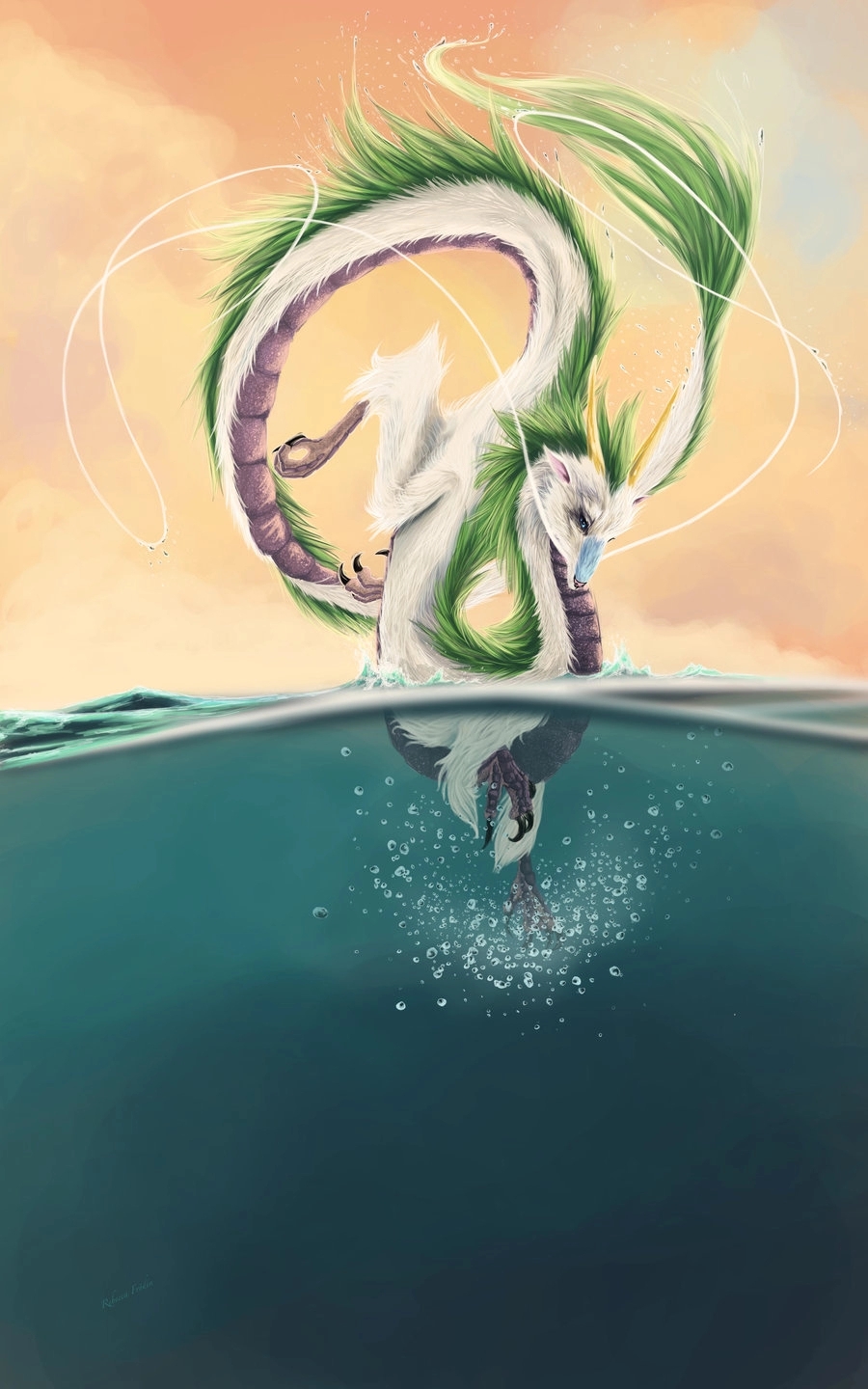

 10
10
_20241115233648A163.jpg)